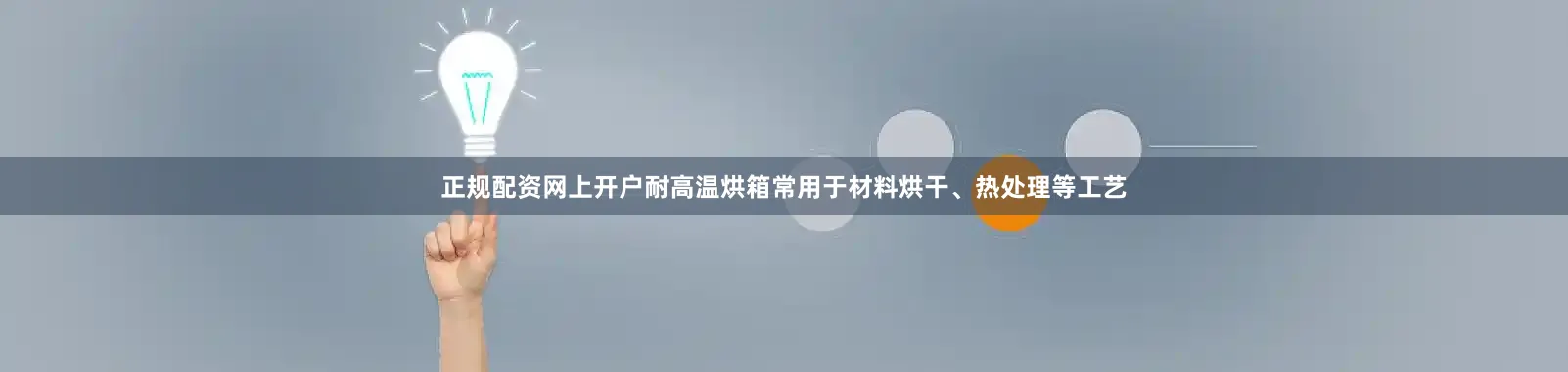《铁甲沉沙录》
黄海之滨的渔人常说,每逢阴雨天气,海底便会传来沉闷的轰鸣。这声响不似雷,不类炮,倒像是某种巨兽在深渊中辗转反侧。直到二零一九年那具锈蚀的钢铁残躯破水而出,人们方知这百年呜咽,原是那艘唤作\"定远\"的巨舰在海底作不平之鸣。
打捞者撬开扭曲的舱门时,腐海的气息裹挟着历史的尘埃扑面而来。一枚嵌在钢板里的弹头,半截绣着\"经远\"字样的铜牌,几枚凝结着盐晶的纽扣——这些零落的遗物在探照灯下泛着幽光,竟使那些惯看生死的考古专家们倏然红了眼眶。有位白发老者抚摸着舱壁上深深的弹痕,忽地背过身去,肩头颤动如风中残烛。
展开剩余59%这艘钢铁巨兽诞生于德意志的船坞,彼时清廷的官吏们正用丝绸袖子擦拭着单筒望远镜,遥望海天交界处。一百四十万两白银堆砌出的庞然大物,有着令东瀛岛国战栗的伟力:七千余吨的躯体披着二十公分厚的钢甲,四门克虏伯巨炮的炮口足以塞进成年男子的头颅。当它劈波斩浪驶入大沽口时,岸上穿马褂的官员们竟错觉大清水师真能\"威震四海\"了。
光绪二十年的秋海战来得比预想更早。日军舰队的炮火将黎明前的海面烧成赤红色,定远舰的瞭望塔上,管带刘步蟾的望远镜镜片映出密密麻麻的敌舰黑影。后来的战报记载,这艘旗舰在六小时内承受了两百余发炮弹,它的钢甲被撕开十七处裂口,甲板上的血水与海水混作粘稠的浆液。最令人骇然的是,当弹药库最终被引燃时,幸存的水兵们不是跳海求生,而是沉默地走向各自战位——他们选择与这具钢铁棺椁共同沉入冰冷的波涛。
威海卫的复制品如今泊在晴空下,光可鉴人的舰桥倒像是出殡时的纸扎。参观者摩挲着仿制的炮管,却不知真品沉没前炮膛里尚卡着未及击发的最后一弹。博物馆的解说词总强调\"亚洲第一巨舰\"的威名,却少有人提及战前三年,户部为给老佛爷庆寿,竟将购弹的款项换成了颐和园的琉璃瓦。那些在底舱操作蒸汽机的工匠之子,至死都不知他们的炮弹比日军少了三成。
暮色中的定远舰投下长长的阴影,恰似历史书里那道未愈的伤疤。但看那锈蚀的锚链上,不知何时已攀满新生的海藻。海风掠过桅杆的呜咽,恍惚间竟化作了汽笛的长鸣。这钢铁铸就的教训终将化作淬火的利剑,而那些在怒海中永眠的英魂,亦会见证后来者以更坚实的甲板,破开新时代的惊涛骇浪。
发布于:山西省盛达优配app-配资导航网-炒股杠杆实盘-配资公司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